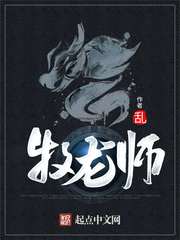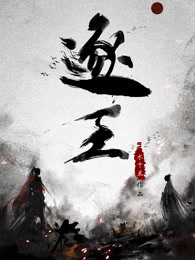去看书>朕真的不务正业 > 第一千零六十章 白天做白日梦,很合理(第1页)
第一千零六十章 白天做白日梦,很合理(第1页)
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,是君臣矛盾的一部分,太子和皇帝,是君臣大于父子。
尤其是太子之位确定后,太子就是代表臣子,跟皇帝打擂台最好的选择,这也是千年以来,一贯的朝堂规则。
对于太子而言,危险如利刃悬顶,一时一刻都不能松懈。
朱常治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,他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,他尚且年幼,而且并不是人中龙凤、聪明绝顶之辈,但他有一个好母亲。
王皇后教给朱常治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,总结而言,让臣子背锅。
王夭灼跟朱常治讲过解缙之死,解缙看起来是臣子卷入了储君争夺的大戏之中,但其实根本上,是朱棣的问题,朱棣自己本身犹豫不决。
朱高煦在靖难之战中,打出了赫赫战功,在武力上,朱高煦更像朱棣,朱棣说那句:世子多疾,汝当勉励之,大约是真心实意。
除了这一句外,在朱高煦封汉王留在南京的时候,朱棣还对朱高煦说了一句:吾望汝,承责于朝。
朱棣在储君人选上的犹豫,让太子朱高炽不得不增加自己的筹码,以求在储君之争获胜,而解缙就成了其中的关键人物,解缙一句好圣孙,让朱棣下定了决心。
可解缙私谒太子,最终触动了皇帝最敏感、最脆弱的那根神经,太子礼贤下士、有口皆碑,想干什么?
王夭灼教给朱常治的办法,就是让臣子背锅。
就这种报还是不报的问题,让臣子说出来,好过让朱常治自己讲出来,这样有了一层缓冲和冗余,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,就不会过分加剧。
“高先生以为,是追欠,还是报灾蠲免?”朱常治看向了高启愚,询问其具体的意见。
高启愚脸上不动声色,可这心里一紧,太子朱常治这追着不放,意思非常明确,今天太子叫他们来,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表态,而且非常明确的那种表态。
高启愚在电光火石之间,就明白了,太子殿下,在找大臣做这个恶人。
而且他是满朝文武里,最合适的人选,太子要是去找李如松,那才是天大的危险,反倒是当初没有避嫌的高启愚,非常适合做那个背锅侠,缓和皇帝和太子的矛盾。
只不过,这个背锅侠极度危险就是了。
高启愚深吸了口气拱手说道:“殿下,臣是礼部尚书,户部的事儿,理当问户部,大司徒和少司徒,都随扈南下松江府,推动一条鞭法六府广布施行,臣说户部的事儿,就是越俎代庖。”
“殿下,朝廷里,这越界是很犯忌讳的事儿,臣不能为。”
高启愚不肯做这个背锅侠,万丈悬崖走独木桥也就罢了,稍有不慎就做了太子的替死鬼,再说了,太子上位,那都不知道多少年的事儿了,他高启愚早就化成灰了。
王皇后的办法很好,唯一的问题就是,朝中大臣人人精似鬼,想找个解缙这样的替死鬼,难如登天。
解缙是主持修撰《永乐大典》,觉得自己深受朱棣信任,才稍微多往前试探了一步,就死的不能再死了。
高启愚给的理由非常合适,这事儿不在他的管辖范围,他胡说,皇帝不生气,大臣们也会生气。
“这话讲的不对,父皇临行前可是说了,申先生和高先生皆可倚重,让孤有事,就多问问二位,高先生这个时候,如此推诿,那是父皇错了?还是高先生不能倚重?”朱常治这个时候,语气已经有些严厉了。
“臣惶恐,臣才疏学浅德行浅薄,不堪大任,让陛下失望了。”高启愚的回答非常的果断。
朱常治立刻意识到,面前的高启愚根本不怕他,而且他有些心急了,话说的有些太急了,太满了,反倒是把自己架了上去。
高启愚只需要写一封致仕的奏疏,措辞柔和一些,把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,皇帝一看礼部尚书要致仕,自然会下章仔细询问。
最后被教训的不见得是高启愚,而是他朱常治。
朱常治这活儿,干的太糙了点儿,陷入了被动,这不能怪他,他才十三岁,这种君臣之间的博弈,他还是第一次接触,没有经验,理所当然。
“孤德凉幼冲,对官场的规矩不是很懂,仔细想想,还是高先生说的有道理,那这件事,就报闻父亲决定是否追欠。”朱常治倒是十分干脆,以自己年纪小,德行修的不够,承认了自己错了。